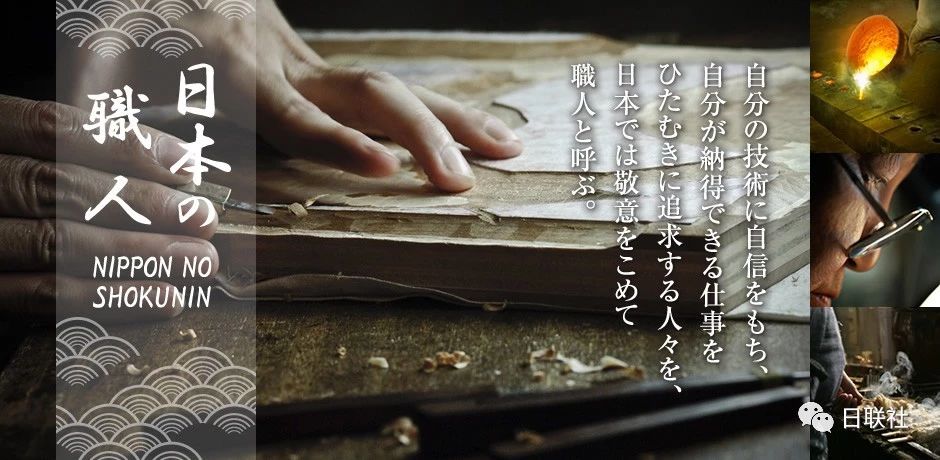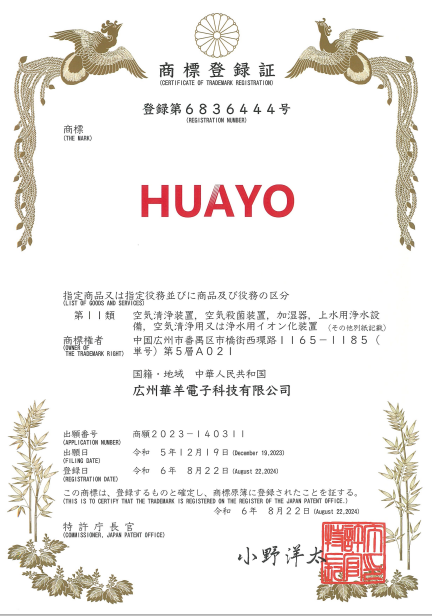“日本没有那么美好,也没有那么恐怖”
作者/图片:李忠谦 来源:风传媒
龙应台基金会11月3日举行思沙龙活动,由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以“历史的记忆、历史的忘却—日本,这个不成熟的民主国家”为题,轻巧而温柔地带着听众一起检视了她对于战争记忆、历史记忆的观察。
阿古教授非常重视教育与批判思考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,不过她也对台下的听众畏惧“强大的日本可能发动战争”感到惊讶。
阿古说,日本人并不像台湾人想到那样团结、那样美好,内部也有很多矛盾与缺点,但她也同样不希望再看到日本发动战争,会以学者的身份继续努力。
战争与历史的记忆,每个人都不一样
阿古教授说,战争与历史的记忆,与每个人的背景密切相关,所以她也介绍了自己的成长背景与经历。
阿古智子其实并非历史或战争的专家,她1971年在大阪八尾市出生,在大阪外国语大学主修中文。后来在香港大学拿到教育学博士后,以一名社会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研究现代社会的变迁,关注留守儿童、维权律师、公民社会等议题。
阿古教授说,她从小在大阪郊区的八尾市长大,那个地方有许多“部落人”(江户时代社会地位最底层的人)、被强迫来日工作的朝鲜人、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留学生、政治犯的孩子。
这样有趣而多样的社会组成,让当地的老师非常重视“反歧视教育”,当时老师编纂使用教材的自由度也比现在高。
可能也是这样的生活经历,阿古说,她在北京的家空间虽然不大,但总会保留一两个空房间,给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学生住。但她也说,可惜大阪的左派传统没有保留下来,如今大阪的政治气氛已经变得非常保守。
阿古教授说,自己原本没有想当老师,而是想到国际的NGO从事一些扶贫的计划。不过到香港大学念书之后,才以一边做计划、一边读书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理解。
阿古后来到中国做田野调查,也同样喜欢深入社会底层,所以她不喜欢跟她的老师辈出访,因为这些学者多半是跟当地官员喝酒,然后取得研究所需的资料,“这样就看不到当地人民比较草根的生活了”。
我的战争记忆
阿古智子教授说,二战的时候她的父母还小,自然不可能上战场,包括她的祖父母同样没有上过战场,她笑着说:“所以我对靖国神社没有什么感情,因为我的家庭没有这种背景。”
但阿古先生的爷爷确实到南京附近打仗。阿古说,她的公公是一位三重县的农民,在中国作战时受伤,中国人救了他之后就被送回日本,“但他从来不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事情”。
阿古的公公自己有两座山,从林业方面的工作。他住的村子非常宁静而朴素,村民都是从事放牧或耕种的工作,不过当战争爆发,村子里三分之二的百姓都上了战场,大家都要为天皇与国家效力。
他们根本不理解纪录片所说的事实:日本在根本不可能打赢的情况下作战。不过阿古的公公是一位自民党的党员,虽然参与并不积极,但为了领取退休金,所以还是选择支持自民党。
“我青春期的很多烦恼,都是这些老太太替我妈妈听的”
阿古也谈到,她在撰写博士论文时,曾在上海一个老妈妈家借住了一年。由于阿古自己的妈妈在阿古初中时因为癌症去世,所以在她成长的过程中,有机缘认识了几位中国的老太太,“所以我青春期的许多烦恼事,都是这些老太太替我妈妈听的”。
阿古教授特别提到上海的老妈妈,因为她在二战时吃过日军的苦,文革后又被斗争的很惨。不过这位老妈妈也是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,总是为了党、为了国家贡献,像阿古老师这样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,她就会负责接待照顾,不过这位老妈妈前两年已经去世了。
周遭人的战争记忆
阿古智子教授说,她因为家人都没有参与战争,所以她的战争记忆都是透过学校的教育(大阪的公立小学、公立初中)而来,还有像是上海老妈妈,甚至从不愿透露他的参战经验的公公。
阿古表示,就算公公什么也不告诉他们,他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事情。有趣的是,阿古教授也介绍了她的8岁儿子的“战争记忆”。
阿古说,他的小孩是东京都中野区的“平和之森小学”的二年级学生。
“平和之森小学”的校地过去是专门关押政治犯、思想犯、无政府主义者、参与工运的老百姓的中野监狱,但如今只剩下美丽的红砖校门还是监狱遗迹。由于日本小学现在都会教授孩子们当地的历史,阿古就问孩子的老师,是不是会教导孩子相关的历史?没想到老师说,这不在国小的教育范围里。
平和之森小学的鸟瞰图。
阿古智子说,如果要知道日本走向战争的道理,包括思想控制的那些黑历史,都应该要去学习跟了解才对。
后来阿古提议在学校办一个工作坊,也画了海报,结果老师还是说“不可以”。阿古问为什么,老师说,这张海报上有纳粹、政治犯等词汇,超出孩子的学习范围了。
阿古批评,为什么日本学校的教育体制会这么样的僵化。
平和之森小学新址内的中野监狱大门。
此外,平和之森小学因为准备迁校,新址上留有的中野监狱该不该拆除,也成为学校与老师、家长争论的话题。
不过许多日本人都抱持着不想“惹争议”的心态,不想跟政治话题沾染上关系。这个案子目前还在中野区讨论,已经开了两次公听会与讨论会,预计11月底才会有结论。
阿古说,日本的教育非常欠缺批判思考,透过对这些遗址的保留与保存,除了可以认识过去,也可以作为举办沙龙之用。
“我觉得日本其实很可怕”,一位现场听众提到,她曾经参加各国军舰在雪梨的活动,在看了不同国家的军舰之后,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日本军舰,最干净、最有礼貌,就算是其他很强的国家,也没有办法达到日本人的有纪律、有礼节的程度——这才是大家最怕日本的地方。如果未来中日还有一战,中国真的打得过吗?
阿古教授在回答时苦笑着说:“你们那么害怕日本人,该怎么办?”
她认为这些对日本人的想法“都是你们的幻想”。她自己看日本人的小孩子根本不守规定,但有一点让她担心的是,日本有许多不合时宜、甚至不合理的规定,但社会都不愿意去改变。
像是公立学校的家长会都在白天举行,这让上班的男性与有工作的妇女都没有办法参加,她曾建议校方改到晚上举行,但校方不愿意改。这到底有什么道理呢?学校也说不出来,只知道一定要遵守,整个日本社会这样的情况非常常见。
从这个角度出发,阿古说“我能理解你们为什么害怕日本人,因为有时候我也害怕。” 因为日本这种集体的惯性让她很不舒服,她认为日本社会应该跟台湾学习比较灵活的态度。
还有听众问到,日本发动侵略战争,又不愿意道歉,跟日本的民族性是不是有关?
阿古老师认为这个问题他很难回答,因为日本也有各式各样的人,在政治问题上也有左派右派的多样观点。日本在国际化之后,像她这样在各国之间跑来跑去的人也很多,也会不习惯日本的传统文化,你们认为日本人很团结,但日本人并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团结。
日本的左与右
阿古说,她这几年开始往台湾跑,对台湾的理解还非常不够。她发现台湾的老百姓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立场,所以要跟台湾人交朋友的时候要非常小心,不要说错话。
而日本左派与右派的立场与争议也是一样,也影响到日本人对战争与相关问题的态度。
自民党一般来说被视为右翼(保守派),重视稳定与现实、传统与秩序,因此同意保留天皇系统、支持国旗国歌、夫妻同姓(太太婚后改为夫姓)、反对外国人的参政权与投票权;立宪民主党与共产党一般被视为左翼(革新派),更重视人权与自由平等,夫妻可各自保有本性,支持外国人的投票权与参政权。
阿古智子教授指出,其实不同年龄层对同一个政党的左右倾向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,甚至可能横跨左与右,像是图中的日本维新会(黄色)在年轻人看来竟然是一个左派政党。(李忠谦摄)
不过阿古教授也提醒现场听众,事实上左与右存在非常多细腻的分别,以上的分类并非绝对,所以对于道德观的冲突应该尽量去了解才对,而不是简单的贴上谁好谁坏的标签。
更有意思的是,左翼与右翼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尽相同,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年龄层也会有不同看法。像是日本维新党是非常右的,但在二三十岁的民众眼里,却是liberal的政党,自民党在年轻人眼中却是一个中间政党。
不过现在日本的右翼比较容易受到支持,左翼比较不受欢迎。可能是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可能闹的太过分了,引来社会的普遍恶感。
慰安妇与假新闻
阿古智子在座谈时聊到台湾先前的慰安妇雕像被踢争议,她说这件事让她感觉非常丢脸,并强调那些都是极右派分子所为,并非一般日本人的态度。
不过她也提到,《朝日新闻》2014年前曾经撤回数十年前的慰安妇报导,因为采访对象吉田清治说谎。这起事件引来右派政府与《产经新闻》等右派媒体大肆攻击,连一般民众都受到影响。
阿古说,她一个朋友的先生是法官,家里因为要帮小朋友订儿童报,她的朋友就选了《朝日》,结果他朋友的先生非常不高兴,说“为什么订这样的报纸”,可见《朝日》的慰安妇报导争议在社会上的影响。
不过阿古也强调,《朝日新闻》的几则报导确实有问题,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慰安妇的相关资讯都是错的。
若把左右之争带入日本宪法的修正争议,这时右翼反倒是“革新”的一派,左翼则是希望保留现有的宪法内容。因为右翼认为现行宪法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(GHQ)所制定,日本应该根据固有传统制定(修改)宪法,第9条当然可以修改,更右的意见甚至希望回复旧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,主权不在民而在天皇;左翼则认为日本现行宪法保有外国的革新思想,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,没有必要修改。
日本左派与右派的问题
自认并没有特定政党偏好的阿古,也指出日本左派的问题:他们常常过度重视中日友好。
像是她很多做中国研究的老师都是偏左,他们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时常常只跟官方打交道,承接一些中日友好的项目。但阿古教授批评,她的这些老师辈并没有跟民间人士打交道,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是假的,不是真的。
阿古说,像她一样关切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研究者,往往都是右派,但这些人的问题是,常常利用研究成果煽动对中国、朝鲜的仇恨,进而歧视这些国家,这也是她无法赞成的。
还有一些日本右翼常跟台湾独立派合作,过度美化日本。阿古教授笑着说:“日本不是那么美好的国家,有很多问题的!”
阿古教授认为,日本的民主主义之所以不成熟,是因为缺少能够独立思考的年轻人,这一点要仰赖教育的变革才能逐渐改善。至于左右之间、或者不同立场的碰撞,则牵涉到彼此是不是能够理性沟通、超越自己的局限。
她在演讲中也提出四个建议:尽量客观了解道德观的冲突、面对事实、尊重专业主义、维持耐性。
她最后呼吁,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主体性,要小心可能会利用你的势力,每个人也要坚持诚实的态度,不要只是考虑自己利益为主的那种立场。
阿古智子。(李忠谦摄)
阿古教授表示,战争是人类的灾难,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种灾难是怎么发生的,否则战争还会再发生。现在日本的媒体时常强调中国与韩国的缺点与反日情绪,这难免让日本的年轻人不高兴,觉得中国与韩国为什么这么仇日。
与此相对,阿古说,东京大学跟北京大学不久前办了一场研讨会,讨论社会弱势的问题。北大学生的程度非常好、讨论能力非常强,但他们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非常好,反倒是冲绳人没有少数民族地位,总是遭到歧视。阿古也批评,北大学生的观点太过简化,这一定程度都是受到媒体与宣传的影响。
对待战争责任,德日为何不同?
对于日本人不愿意承认战争责任的问题,阿古说也有很多日本人承认战争的责任,日本政府(尤其是社会党执政的年代)过去也曾经道过歉。
至于为什么日本与德国对待战争责任的态度有所不同,阿古认为跟冷战时期的局势有关。
日本选择跟美国合作,站在资本主义阵营反对共产主义,这一点跟台湾很像。阿古说,台湾人会那么喜欢日本,其中也有冷战的因素。德国在战后随即开始赔偿、教育的工作,但是日本战后跟中国分属两个阵营,就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一件事。1970年代的中日交流与友好并不是民间自发,而是双方政府基于外交需要所营造出来的,战争的相关问题还需要民间与政府一起努力,民主国家也应该一起合作对抗反民主的因素。
采访侧记:日本人(该)是什么样子?
在阿古教授的演讲之前,现场先播放了一支纪录片—《石原莞尔将军:发动战争的男人》,讲述“大东亚战争”的理论指导者石原莞尔中将的故事。
正当观众沉溺于一位日本将军发动侵略的理论与现实之中,一位个子娇小的东大教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刚才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,我自己作为日本人,觉得有一点害怕、有一点恐怖。”
这位教授正是当天活动的主角人阿古智子,她说,日本人并不常看这样的战争纪录片,日本的小孩子也不怎么有机会看,所以觉得比较恐怖。
从这个看似闲聊的开场,却点出了一项事实。距离今日已超过70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,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人真的亲身经历。
而日本人与台湾人对于中日战争的面貌与记忆,在不同的历史教育与政治宣传之下,真的会指向同样一组历史事件吗?
年龄在73岁以下的中日民众,其实就根本没有机会亲自见证二战,大家都免不了是透过教科书、各种媒体与口耳相传,来理解中日战争。
作为日本的邻国、以及曾被日本侵略与殖民的国民,看了讲述日军参谋如何谋划发动侵略战争的纪录片,感觉当然不怎么好受,现场也有好几位听众表达了对强大日本的恐惧、以及对日本可能再次侵略邻国的担忧。
经常造访中国、先生也在北京担任驻外记者的阿古教授说,台湾人对日本的印象让她很意外,日本人没有那么厉害、那么团结,但她也希望日本更多些灵活性,不要只知道服从与守旧。
透过纪录片所展现的日本将军形象,跟眼前这位实际站在眼前的日本学者,那个才是我们印象里的日本人?那个才是日本人的真面貌?
除了阿古所说的“日本也有各式各样的人”,也如同现场一位听众所说的,阿古教授给人的感觉“是个不太像日本人的日本人”。
如果有更多像阿古教授这样理性的声音能够发挥力量,也许日本的邻国也不用在二战已经结束的七十多年后,还要继续“抗日”。